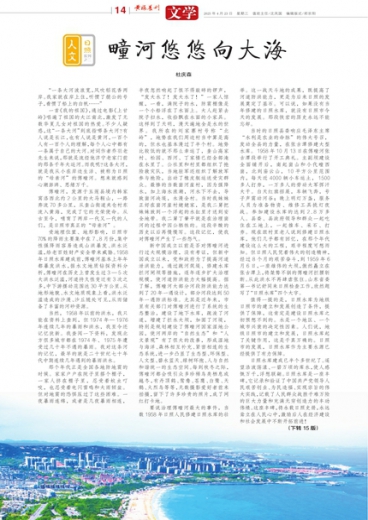杜庆森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一首《我的祖国》,通过电影《上甘岭》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激发了无数华夏儿女对祖国的热爱。不少人疑惑,这“一条大河”到底指哪条大河?有人说是长江,也有人说是黄河,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理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大河。对词作者乔羽老先生来说,那就是流经他济宁老家门前的那条千年大运河。而我呢?这条大河,就是我从小在岸边生活、被称为日照的“母亲河”的傅疃河。想来就感到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傅疃河,发源于五莲县境内韩家窝洛西北约2公里的大马鞍山,一路奔流70多公里,从奎山街道夹仓村东流入黄海,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从古至今,哺育了两岸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是日照市真正的“母亲河”。
受地理位置、地形影响,日照市70%的降雨主要集中在7、8月份,集中性强降雨容易造成山洪暴发、洪水泛滥,给老百姓财产安全带来威胁。1958年日照水库建成前,傅疃河基本上年年都暴发洪水,据水文地质钻探资料分析,傅疃河在历史上曾发生过3—5次大洪水泛滥,河道持久性变迁有3次之多,中下游摆动范围达30平方公里。从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现象上看,洪水泛滥造成的沙漫、沙丘随处可见,从而储备了丰富的河砂资源。
当然,1958年以前的洪水,我只能在资料上查到,但1974年—1976年连续几年的暴雨和洪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查阅一下资料,发现北方很多城市都在1974年、1975年遭受过几十年不遇的暴雨。我对这条河的记忆,最早的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连续几年遇到的暴雨洪水。
那个年代正是全国各地防地震的时候。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搭个棚子,一家人挤在棚子里,忍受着蚊虫叮咬,也忍受着电闪雷鸣和大雨倾盆。但对地震的恐惧压过了这些困难。一夜暴雨连绵,或者是几夜暴雨相连,半夜忽然响起了恨不得敲碎的锣声,“发大水了!发大水了!”一家人惊醒,一看,满院子的水,防震棚像是一个小船浮在了水面上。大人赶紧去院子扫水,收拾飘在水面的小家具。这样到了天明,漫天遍地全是水的世界。我所在的刘家寨村号称“北岭”,地势在我们周边村当中算是高的,但水也基本漫过了半个村。地势比较低的就不那么幸运了,奎山高家村、松园、西河、丁家楼已经全部淹在水里了。公社里和村里都组织了抢险救灾队,当地驻军还组织了解放军参与抢险,出动了橡皮艇运送受灾群众。最惨的当数崮河崖村,因为强降水,加上海水涨潮,河水下不去,导致崮河决堤,水漫全村。当时我妹妹正好在崮河崖村姥姥家,是我二舅把妹妹放到一个浮起的水缸里才送到安全地带。我二舅丁肇平就是在治理崮河的过程中因公牺牲的。这段辛酸的历史以后再慢慢写。这段记忆,使我对傅疃河产生了一些怨气。
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否对傅疃河进行过大规模治理,没有考证,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了提高河道泄洪能力,通过疏河筑堤、修建水库拦河闸坝等措施,逐年逐步扩大治理规模,使河道防洪能力大幅提高。据了解,傅疃河大部分河段防洪能力达到了20年一遇设计,部分河段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尤其是近年来,市里有关部门对傅疃河进行了系统的生态整治,建设了地下水库,疏浚了河道,增建了拦水大坝,加固了河堤,特别是规划建设了傅疃河国家湿地公园,使河两岸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有了很大的改善,形成湿地与海洋、森林相互补充、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凸显了生态型、环保型、人文型、碧水蓝天、绿树环抱、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空间。每到秋冬之际,傅疃河都会吸引众多珍稀鸟类栖息或越冬,有丹顶鹤、鸳鸯、苍鹰、白鹭、天鹅、火烈鸟等等,无数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成了网红打卡地。
要说治理傅疃河最大的事件,当数1958年日照人民修建日照水库的壮举。这一战天斗地的成果,既提高了河道防洪能力,更是为后来日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修建的日照水库,就没有日照市今天的发展。那段恢宏的历史永远不能忘却。
当时的日照县委响应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伟大号召,发动全县的力量,在张古潭修建大型水库。1958年10月13日在傅疃河张古潭段举行了开工典礼。主副坝建设全面铺开后,南起崮山和小代疃西崮,北到庙云山,10平方公里范围内,每天近4000辆小车运土,1500多人打夯,一万多人的劳动大军挥汗大干。白天红旗招展,车辆飞奔,号子声震动河谷;晚上明灯万盏,服务人员为准备物资、维修工具挑灯夜战。参加建设水库的达到 2.8万多人。县委、县政府领导和群众一起吃住在工地上,一起推车、采石、打夯。现在跟村里老人说到修建日照水库,他们几乎都有回忆,在那个年代建设这么大的工程,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日照人民凭着伟大的创造精神,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斗,到1959年6月6日,一座雄伟的大坝,傲然矗立在张古潭上,将桀骜不驯的傅疃河拦腰斩断。从此洪水不再肆虐张狂。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来日照检查工作,欣然题写了“日照水库”四个大字。
值得一提的是,日照水库为地级日照市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这肯定是建设日照水库之初预想不到的。水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人们说,地级日照市的建立和发展,日照水库起了关键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日照市的发展,日照水库作为主要水源已经提供了有力保障。
日照水库建成已半个多世纪了。遥望浩波荡漾、一碧万顷的库水,使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日照水库是一座丰碑,它记录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创业、为民造福、实现宗旨的伟大实践,记载了人民群众战胜千难万险的巨大力量和充满无穷创造力的丰功伟绩。这座丰碑,将永载日照史册,永远耸立在人民心中,激励后人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不断开拓前进!
前几年假期,我曾多次和家人一起去日照水库参观,仰望日照水库纪念塔,塔基上四个浑厚有力的宋体字“降龙伏虎”,那个“虎”字因为是异体字,好多人还不认识。瞻仰“日照水库”四个大字,心中对舒同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马背书法家”,并且具有崇高革命风范的革命前辈,充满了深深敬意。我同时也去参观了日照水库纪念馆,这是时任陈疃党委书记、我的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学弟推动建立的,成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阵地。展馆详细介绍了那段光辉的战斗历程,让我强烈感受到了日照老一代领导人李鲁生、牟步善、庄茂禄等前辈们的丰功伟绩,特别是牟步善老书记。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多次见过老人家,并且在参加日照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时同在一个小组讨论,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文艺演出时,我还专程采访过他。老领导那种精气神、那份激情、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让我们这些晚辈敬佩,是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精神财富。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人与河流之间从来都是十分密切的。有水才有河,有河才有人,有人才有了一切。自远古时代起,人类便本能地择河而居,河流宛如大地的血脉,静静流淌,孕育了璀璨的人类文明,为人类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人类也在趋利避害,治理水,用好水。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展现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当然还有奉献和牺牲精神。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至今都还在发挥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还有秦国修郑国渠,本来是韩国谋士郑国出的计谋,意图是通过修渠来消耗秦国,但没想到却使秦国获得了大量可浇灌的土地,有了充足的粮食,壮大了秦国的国力。到后来历朝历代对大江大河的治理,都充分体现了对水的重视和炎黄子孙的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治山治水的热潮。日照水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工程,哪有我们现在城市的繁荣和工业发展?看今天,沿着一条条河的流域,村庄如繁星般散落,城市迅速崛起,它们见证着人类与水的不解之缘。而在日照,傅疃河便是这样一条承载着万千故事与情感的母亲河。它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贯穿了日照的南北与西东。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也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文明。
在傅疃河的沿岸,还有一些古老的遗址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小代疃遗址,那是历史的厚重沉淀,仿佛能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远古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他们依傍着傅疃河,汲取着河水的滋养,创造出独特的文明,开启了人类与傅疃河共生共荣的篇章。吕母崮遗址,承载着一段激昂的历史传奇,在那烽火硝烟的岁月里,傅疃河见证了英雄儿女的豪情壮志,它的流水仿佛也在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吟唱。夹仓古镇,宛如一颗镶嵌在傅疃河畔的明珠,悠悠岁月中,它凭借着河流带来的便利交通和丰富资源,发展成繁华的商贸重镇。紧扣傅疃河北岸,傅疃河大桥桥头西边约50米,立着一块2009年日照市人民政府立的石碑“日照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氏家族墓群”,这是金代状元张行简家族的墓地,选在了他建立的“魁文书院”旧址的前边,百年之后依河而居,确是风水宝地。傅疃河宛如一位默默的守护者,见证着这里的兴盛与繁荣。疃河悠悠,道不尽的故事与回忆。河水奔流,说不透的魅力与期待。
傅疃河的自然风光,同样如诗如画,令人陶醉。清晨,阳光初上,洒进树林,斑斑点点,梦幻般的感觉。空气湿润清新,岸边树木繁茂,郁郁葱葱,像是给大地披上了一件翠绿的锦袍。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鸟儿在树梢跳跃欢叫,仿佛在演奏着一曲自然的乐章。或看水鸟翔集,它们或在空中盘旋翱翔,或在水面上轻盈掠过,时而发出清脆的鸣叫,为傅疃河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鱼儿在清澈的河水中畅游,它们灵动的身姿清晰可见。我也曾在夕阳西下时漫步大堤,看半天晚霞铺洒在水面,体验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奇观,也领悟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如是秋冬季节,那满河堤的芦苇,随风飘浮,又有了“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场景。
有水则有竹。傅疃河两岸的竹林茂盛,独为一景。城西有竹洞天风景区,那是日照南竹北移最成功的范例,和南茶北移、南稻北移一样,都是日照人民艰苦奋斗的写照。竹洞天风景区我去过多次,既听过春夏竹子拔节的声音,品尝过竹笋的美味;也看过冬日大雪纷飞时,修长的竹子在风雪中摇曳生姿,让人不禁沉醉在这宁静而优美的氛围之中。
在傅疃河南岸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叫牟家小庄,依河而居,风景秀美。这里是一个红色故地,留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足迹,这里是1928年中共日照县委成立以来最早的3个党支部之一,这里也是1932年日照暴动的发源地之一,走出了曾任日照县委第一任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副省长的老革命家陈雷(原名牟春霆),革命家、诗人牟宜之,牺牲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军飞行员牟敦康烈士等一批名人。我曾多次前往牟家小庄参观,村子在傅疃河边建有一个小院子,叫竹林馆,里边竹林茂盛,水波荡漾,小桥流水,颇为悠闲。村里也正在以此规划一个农村生态休闲度假园,建成后必将为傅疃河两岸增添又一景观。我曾经为竹林馆题诗:
竹里馆,大河边。听竹声,望奎山。戏水乐,垂钓欢。小庄大,乡情牵。
傅疃河最下游是夹仓。夹仓因“两所夹一仓”而得名,是傅疃河长期冲积而成,傅疃河从此入大海,留下风流一路歌。这里土地肥沃,特产丰富,人杰地灵。曾是日照八大海口之一,素有“日照城南巨镇”之称。据《青州府志》记载,元代已有巡检司设于夹仓,距今约七八百年,明清时期晋陕商人云集,形成“佟公义集”,店铺林立,非常繁华。元代为海防重地,清代筑石成墙,设立四门:东北门“聚奎”,西北门“宗岱”,东南门“表海”,西南门“望沂”。现存日照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也就是当时夹仓小学和联中所在地。我曾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那个关帝庙原来被改造成了学生教室,后边的大殿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在大殿东旁搭建了一间小偏屋,就是我和同事的宿舍兼学校的广播室,每天早操就是在这里放的唱片。“第六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这声调现在还在耳边回响。
在夹仓学校工作的时光,是我人生当中一段最难忘而快乐的记忆。我毕业时才十九岁,正值大好青春年华。我担任初一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语文,一百多个学生。因为学生作业比较多,晚上要加班批作业。为了不影响同事休息,我用自己的黄书包(那时是最流行的)挡着白炽灯,时间长了闻到一股煳味,原来是把书包烤煳了。等到夹仓逢集时,我便找了个裁缝把那块地方补了个补丁,想想那段岁月真值得怀念。
一条大河,奔流向海,势不可挡。它寄予了人们美好的希冀,也留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傅疃河,是日照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家乡人心灵的寄托。在未来的岁月里,愿傅疃河继续奔腾不息,流淌着生命的力量,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一道,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正是:
疃河奔流向大海,初光普照情满怀。
上善若水育生命,乘风破浪向未来。
奎山脚下立大志,人生航程筑高台。
悠悠岁月长河伴,经山历海从头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