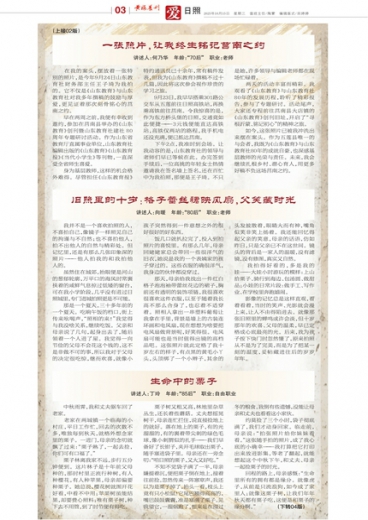讲述人:何乃华 年龄:“70后” 职业:老师
□ 全媒体记者 王蓓蓓
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日照人的微信朋友圈,成了一座流动的“人生影像馆”。
有人晒出旅途中“光线与心情刚刚好”的美照,有人调侃旅行里“错误选择堆砌的不后悔”,还有人翻出二三十年前的老照片——— 画面里父母眼角无纹,旧友相拥大笑,连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都停留在拍照时的笑容里。
这些被反复翻看的“人生照片”,撕开了一个温柔的真相:真正值得纪念的时刻,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至高处”,而藏在生活近处的小“转角”。或许是校园走廊的偶然留影,或许是未摆好姿势就按下的快门,没有精致构图,却在日后成为重返时光的“绳结”。
当我们在相册里点开这些照片,实则是与过去的自己重逢。那些欢笑、狼狈、遗憾的瞬间被定格,最终拼凑出“人生真谛藏于偶然”的答案——— 原来最珍贵的时光,早已被不经意的快门,妥帖存进了时光机。
近日,记者按照年龄差异,聆听日照市民用一张照片向我们分享的人生故事。
四十年光影里的家与乡愁
讲述人:贾立明 年龄:“60后” 职业:新闻宣传与民俗研究
我是莒县一名摄影爱好者,与相机的缘分一牵就是40多年。从新闻宣传岗位上用镜头记录家乡变迁,到私下里用数万张照片封存家人的温情,相机于我,早已不是冰冷的器材,而是串联岁月的针线。
第一次为父母拍照是1985年夏天,借了朋友的海鸥双反相机,按下快门时手还发颤。后来自己买了胶片相机,可胶卷、冲印开销不小,照片格外金贵,只在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里拍。
2004 年我换上了数码相机,2008年拍照手机又成了新伙伴,按下快门的成本低了,记录的热情更高了。我开始追着日子拍——— 拍县城街道变宽,菜市场的烟火气,更定格父母和孩子:父亲浇花的背影、母亲揉面的双手、孩子背上书包的雀跃。
日积月累,为家人拍下的照片竟有了两万多张。最难忘的是为父亲记录生日的 15 年。2005年,父亲68岁生日,我第一次用数码相机记录;此后每年这一天,镜头都会准时等候,直到 2021年他84 岁生日。唯独2009年的相册里留了空白——— 那年母亲因腰椎病住院手术,父亲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任我们怎么劝,都执意说“生日不重要,你妈好起来才是真的”。
父亲的一生也像一卷值得细品的胶片:1955年参加工作后,先在讲台上站了30多年,后来又一头扎进党史研究里,一直和母亲住在县城的老房子里。2022年4月,这卷胶片停在了最不舍的一页,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
2024年,我把对父亲的思念整理成纪念文集《吉光片羽》,文集设《父亲的年轮》串起15年生日影像,《生命的年轮》主题精选40年间80张照片,几乎覆盖他每一年的生活片段。2025年,我又整理续集,在续集里安排《母亲日常生活集锦》,选取40多年来每年每月代表性照片102张,截稿于6月28日,这份记录,我想一直继续。
最满意哪张照片?我说没有“最”,只有“每一张”——为父母拍的每一张,都是我人生里最珍贵的作品。夜深人静翻看这些光影,故去的父亲仿佛还在灯下读报,健在的母亲正笑着递来水果,温情满溢。
其实摄影的本质,就是凝固溜走的瞬间。记录社会进步重要,不错过亲人的每一个平凡日常也很重要——— 毕竟这些藏在光影里的温暖,才是岁月最珍贵的礼物。 在我的案头,摆放着一张特别的照片,是今年9月24日山东教育社财务部主任王子琦为我拍的。它不仅是《山东教育》与山东教育社对我多年撰稿的鼓励与厚爱,更见证着那次刻骨铭心的莒南之约。
早在两周之前,我便有幸收到邀约,参加在莒南县举办的《山东教育》创刊暨山东教育社建社80周年专题研讨活动。作为山东省教育厅直属事业单位,山东教育社编辑出版的《山东教育》报》《当代小学生》等刊物,一直深受全省师生喜爱。
身为基层教师,这样的机会格外难得。尽管担任《山东教育报》特约通讯员已十余年,常有稿件发表,但我为《山东教育》撰稿不过十几篇,因此将这次参会视作珍贵的学习之旅。
9月23日,我早早搭乘301路公交车从五莲前往日照高铁站,再换乘高铁前往莒南。令我惊喜的是,作为东方桥头堡的日照,交通竟如此便捷——— 3元钱便能直达高铁站,高铁仅两站的路程,我手机电还没充满,便已抵达莒南。
下午2点,我准时到会场。让我动容的是,山东教育社的领导与老师们早已等候在此。办完签到手续后,一位高挑的年轻女士热情邀请我在签名墙上签名,还在百忙中为我拍照,那便是王子琦。不只是她,许多领导与编辑老师都在现场忙碌着。
两天的活动丰富而精彩。我观看了《山东教育》与山东教育社80年的发展历程,聆听了精彩报告,参与了专题研讨。活动尾声,大家还专程前往莒南县大店镇的《山东教育》创刊旧址,开启了“寻根沂蒙、铭记初心”的精神之旅。
如今,这张照片已被我冲洗出来摆在案头。作为五莲县唯一的与会者,我既为《山东教育》与山东教育社80年的成就自豪,也深感基层教师的光荣与责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潜心育人,用更多好稿不负这场莒南之约。
旧照里的十岁:格子蕾丝裙映风扇,父笑藏时光
讲述人:向暖 年龄:“80后” 职业:老师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不喜拍自己,像镜子一样照见自己的拘谨与不自然;也不喜拍他人,拍不出他人的自然与精彩处。但记忆里,还是有那么几张印象深的照片——— 他人拍我的和我拍他人的。
虽然住在城郊,抬眼便是河山的葱郁轮廓,万平口的海风时常裹挟着的咸鲜气息掠过低矮的窗台,可在我小学阶段,几乎没有进过日照城里,专门进城拍照更是不可能。
那是一个夏天,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吃晌午饭的档口,街上传来吆喝声,“照相的来!”我觉得与我没啥关系,继续吃饭。父亲和母亲说了几句,起身出去了,随后领着一个人进了屋。我觉得一向节俭的父母不会花这个钱的,这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所以我对于父母的决定很吃惊,继而欢喜,就像小孩子突然得到一件意想之外的很好很好的好东西。
饭几口就扒拉完了,投入到拍照片的喜悦里。有那么几年,母亲回姥姥家总会带回一些很洋气的旧衣,她说是我的一个表姨家的孩子穿过的。这些衣服的确很洋气,我身边的伙伴都没穿过。
那天,母亲给我找出一件红白格子泡泡袖带蕾丝花边的裙子,胸前还有透明的装饰项链,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件衣服,以至于随着我长高不那么合身了,也忍着不适穿着。照相人拿出一串塑料葡萄让我拿在手里,背景是墙上的古装连环画和电风扇,现在想想为啥要把电风扇做背景呢,好笑得很。电风扇可能也是当时值得出镜的高档品吧。这张照片就此定格了我十岁左右的样子,有点黑的黄毛小丫头,头顶绑了一个小辫子,其余的头发披散着,眼睛大而有神,嘴角似笑非笑上扬着。我还能回忆得起父亲的笑意,母亲的话语,仿如昨日,只是父亲已不在这世间。镜头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温暖,没有滤镜,没有修图,真实又自然。
我拍得好看的,多是我的娃——— 大娃小时游玩的模样:上山拾栗子、骑行到海边、包汤圆、做甜品;小娃的日常片段:做手工、写作业、在学校里奔跑嬉闹。
影像的记忆总是这样直观,看着看着,当时的笑声、光影就会漫上来,让人不由得陷进去。就像那张旧照里的蝉鸣或许会淡,但十岁那年的欢喜、父母的温柔,早已定格成心底最亮的光。后来,我为孩子按下快门时忽然懂了,原来拍照从不是为了完美,而是为了把某一刻的温度,妥帖藏进往后的岁岁年年。
生命中的栗子
讲述人:丁玲 年龄:“85后” 职业:自由职业
中秋雨霁,我和丈夫驱车回了老家。
老家在两城镇一个临海的小村庄,平日工作忙,回去的次数不多,唯独每到秋天,就格外想念家里的栗子。一进门,母亲的念叨就飘了过来:“栗子熟了,一起去捡,你们可有口福了。”
栗子林离我家不远,步行五分钟便到。这片林子是十年前父母种的,那时村里正流行种树,有人种樱花,有人种苹果,母亲却偏要种栗子。她总说,樱花树就图开花好看,中看不中用;苹果树虽能结果,却要费心照料;唯有栗子树,种下去不用管,到了时节便有得吃。
栗子树又粗又高,林地里杂草丛生,还长着些蘑菇。丈夫想摇晃树干,母亲连忙拦住,说直接捡地上的就好。落在地上的栗子,有的光溜溜的,有的裹着带尖刺的绿色毛球,像小刺猬似的扎手——— 我们早备好了长钳子,夹开毛球取出栗子,随手塞进袋子里。母亲还在一旁念叨:“咱日照的栗子,又大又好吃。”
不知不觉袋子满了一半,母亲嫌提着沉,便把栗子倒在地上,接着往前捡。忽然传来一阵窸窣声,我还以为是栗子掉了,抬头一看,枝头上竟有只小松鼠!它尾巴翘得高高的,嘴巴鼓鼓囊囊,准是塞满了栗子。见我望它,一溜烟跑了,想来是在囤过冬的粮食。我倒有些遗憾,没能让母亲和丈夫也看看这小家伙。
约莫捡了三个小时,袋子彻底满了,我们才动身回家。临走前,母亲说:“拍张照片给你妹妹看看。”这张随手拍的照片,成了我心底的小确幸——— 我打算把它打印出来放进影集,等老了翻起,就能想起这个中秋下午,和丈夫、母亲一起捡栗子的时光。
回程的路上,母亲感慨:“生命里所有的拥有都是缘分。就像虎子,从前是只流浪狗,如今成了家里人;就像这栗子树,让我们年年秋天都有栗子吃,这便是和栗子的缘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