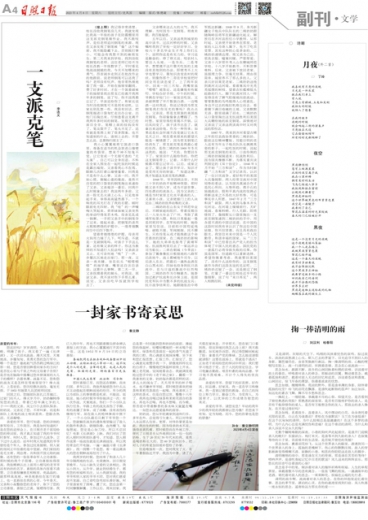李连义
(接上期)我记得非常清楚,校长没收我钢笔没几天,我就发现比我高一年级的孩子在防震棚里用这支派克钢笔做作业,我不敢吱声,是怕老师追问钢笔的来源。现在父亲发现了钢笔被“偷”这个秘密,我不能隐藏下去,否则挨打事小,可能会有我想不到的麻烦发生。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找到没收我钢笔的老师,这位老师已经不当校长改教一年级数学了,平时看见他战战兢兢的我,今天不知哪来的勇气,昂首阔步走到正在批改作业的他跟前,说老师钢笔可以还我了吗?老师没有吭声,他非常热情地看了我一眼,开始在抽屉里翻找,费了好多时间,才在一个装着破袜子的抽屉里找出那支已经离开我两年多的钢笔,说了句,你不说我都忘记了,早该还给你了,和家长说当时没收钢笔可不是别有动机,让家长别乱想一些。我没有回话,把钢笔揣进口袋匆忙走出办公室,出校门后掏出来,仔细查看这支离开我两年多时间的钢笔,发现它已经面目全非,笔帽上面的挂钩没有了,笔尖裂开了,笔头不见了,还有就是笔筒上刻了很多图案,也不知道刻的什么,谁刻上去的。不管怎么说,总算物归原主了。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装进口袋里,准备在适当的机会放进山墙壁龛的布袋里,想来个神不知鬼不觉,让它变成一个无据可查的“无头案”,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不料在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是露出端倪,父亲看我心不在焉,眼睛几次盯着山墙壁龛看,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父亲一问,我开始心慌,做贼心虚的缘故,竟然不自觉的把口袋里的钢笔掏出来递给了父亲,父亲端详一番后,问我什么时候拿去的?我说两年多前。父亲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只见他举起手来,举得高高猛然落下,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我的右腮,顿时眼前电光四射,我“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弟弟妹妹被父亲突然的举动吓得呆若木鸡,母亲见乱成一锅粥,一手把父亲手中的钢笔夺了过来,提起水壶,把钢笔扔进烈火熊熊燃烧的炉膛中,一缕青烟飘向空中后四下散开。
望着青烟缕缕的炉膛,母亲用火钩用力捅了几下,呵斥道,不就是一支破钢笔吗,对孩子下手这么重,还有做父亲的样子,你这当教师的不知道打人犯法吗!父亲欲言又止,无可奈何地“唉”了一声,步履沉沉地走出家门。那一夜,父亲一夜未睡,坐在炕头“啪嗒啪嗒”的抽旱烟,嘴里还自言自语说,这算什么事啊。第二天一早,父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对我说,原谅父亲,我不该对你下手那么重。说完,父亲没吃早饭就到学校去了。
父亲哪来这么大的火气,我不理解。为何因为一支钢笔,彻夜未眠,我百般疑惑。
五年以后,父亲送我到城里的高中读书,过汶河桥的时候,父亲嘱咐我到了学校一定好好学习,全校六十多名毕业生才考上你们五个,说明你还是有实力的,学习还是勤奋的。停了停又说,咱农村人要出人头地,一是当兵,二是考学,想要离开这片靠天吃饭的土地没有其他别的办法,即便考不上大学也要学习,靠知识改变农村的现状,别像你那个二哥在学校里把时间全用在谈恋爱了,上了两年农中,回来一问三不知。我嘴里虽“嗯嗯”地答应,还是嫌他有些絮叨。学校办好手续,中午的时候,爷俩在学校门口一家饭店吃饭,父亲破例要了半斤散装白酒,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说,你还记得因为那支钢笔我打你耳光的事吗?我点点头。父亲说,那是支原装的美国派克钢笔,你却偷偷拿去糟蹋了。当时想,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以后风向变了,孩子读书出息了,就拿出来送给他,作为一种传承;如果还是社会环境不改变就让它永无见天之日。现在看来原来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了,因为那支钢笔已经消失了。那支派克笔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是你二姨奶奶1960年冬天送我的,她说:“天佑,你要回乡下了,家里没什么能给你的,你把这支钢笔带上,记着,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学习。以后,成家立业了,要让孩子读书学习,知识才是受用无穷的财富。”知道这事,我才知道这支派克笔的渊源。
1948年,爷爷因病去世,不到三十岁的奶奶开始精神恍惚,那时候父亲不到八岁,成为不谙世事、四处漂泊的流浪儿。因为父亲的二姨是当时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又喜欢小孩,父亲姥娘门上的人决定由二姨奶奶抚养幼稚的父亲。
二姨奶奶在山东女子师范毕业后,不顾家庭的阻拦,带着皮箱自己一人坐火车去了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和抗日英雄赵一曼是同班同学。在军校的时候,她给家里写信说,目前的中国苟延残喘,破败不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只有投笔从戎才能挽救这个命若悬丝的国家。在二姨奶奶的影响下,她的大弟弟也报考了黄埔军校,抗战胜利里后去了一家远洋公司当船长;二弟在朝城(今莘县)参加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后改姓牛,战士都喊他牛司令,以后进入东北,把最后一滴热血洒在白山黑水间;四妹也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在与日寇的激战中壮烈殉国。二姨奶奶作为巾帼豪杰,她参加过淞沪抗战和长沙保卫战,是国民党军队中为数不多的抗战女兵;抗日战争结束后,她跟随张治中将军抵达新疆;1949年9月,身为新疆女子炮兵中队队长的二姨奶奶跟随陶峙岳将军在新疆迪化起义,解放后在齐河县担任小学教师。从那时起,父亲便开始寄养在那里,老家的人以为寄人篱下,免不了吃苦受罪。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二姨奶奶通情达理,视父亲为己出,浆洗衣服,嘘寒问暖,严管厚爱,父亲十六岁那年考入山东聊城师范学校,十八岁开始教书。不料世事难料,后来,父亲被下放回老家,虽据理力争,但毫无结果,理由很简单,城里养不了那么多的人,父亲只好回莱芜老家。二姨奶奶送他到黄河北边河堤,看着寒风中光秃秃摇摆的树枝,望着衣衫褴褛低头赶路的行人,脚下的黄河同人一样变得没有了脾气轻缓地向前流动,零零散散的鸟鸣搅得人心烦意乱,身边开过去的拖拉机绝尘而去。看着脚下满目疮痍的土地,父亲默默无语,眼里浸满了泪水,二姨奶奶从口袋里掏出这支抗战胜利后美国大兵赠给她的派克钢笔,深情地对父亲说了父亲送我读高中时又对我说的那些话。
1987年,我来到齐河看望古稀之年担任县政协常委的二姨奶奶,眼前这位精神矍铄、耳聪目明的老人还有当年女子炮兵队队长飒爽英姿的影子,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起那支派克钢笔的来历,口齿伶俐的二姨奶奶娓娓道来:抗战胜利后,因为国共摩擦不断,为落实重庆谈判制定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开始“三方和谈”,作为当时新疆“三方和谈”文字记录员,认识了一位讨厌战争、爱好和平的美国大兵詹姆斯,两人经常交流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共真诚合作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必将断送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可是事实非人所愿,1947年2月“三方和谈”破裂,两人来到乌鲁木齐头屯河边,在河堤上缓缓前行,天旷地阔,春寒料峭,行人无踪。即将惜别了,詹姆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递到二姨奶奶的手中,用含混不清的中国话说道,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有幸认识了你这位中国姑娘,你不但贤惠,而且具有政治眼光,我坚信未来中国是一个人民勤劳、和谐幸福的国家,从“三方和谈”中已经看出共产党人的担当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国民党的一意孤行必将导致失败的后果,你虽是国军,但道路可以重新选择,希望你慎重考虑。我就要回美国了,没有什么送给你的,这支钢笔就作为我们这段友谊的见证吧。二姨奶奶迟疑了一会,还是接过了钢笔,打量了一番这位相处近半年的詹姆斯,说了句“来日再见”,两人相拥而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