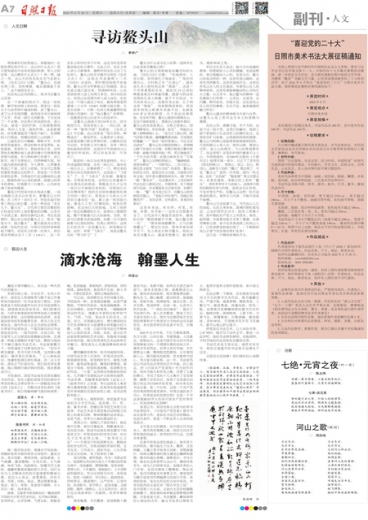李学广
我指着村后的那座山,恭敬地问一位脸色黑红的中年人:这山叫什么名儿?我只想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称谓。那人立即回答:这山哪有什么名儿?!我一愣,随之一笑,这山不但有名而且名气还很大呢。《安东卫志》记载:“鳌头山,在城东南三里,顶有烽墩,墩兵建旗鼓于其上。”这个城指安东卫。
站在岚山区凤阳路上,我为寻访鳌头山而来。
在一个孩童的指点下,绕过一处院落,解开铁丝网上的挂钩,我穿过一段乱石子与杂草碎叶铺成的路,进了鳌头山。进了山才发现西麓,竟然因为采石被挖掉了大半,形成一面巨大的断崖,下方还成了一个水塘,对此我只有深深叹息。进山不远,就是一层防护网,已经被推倒残缺,再向上又是一道防护网,这是新建的,好在断崖弧顶下端有个缺口,有清晰的人行痕迹,我确信找到上山的路了。
山道在岩石中蜿蜒,崎岖不平,时常被荒草遮盖住,两边的树木多是黑松,虬枝盘旋,苍劲有力,看起来很古老。这些黑松在瘠薄的地儿或者岩缝中尽情展现着坚韧与顽强,有几株松树已经倒下,皮已脱尽,枝干光滑枯白,仍然峥嵘不屈,给人超凡脱俗的感觉,令人肃然。山草藤条等虽已干衰,因无人收割,完全可以想象到夏秋茂盛生长的样子,那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当我独自行走这静寂的山道上,踏着松涛与山风的韵律,闻着山间草木的香味,时值腊月三九寒天,心内却充满了浓浓的暖意。
鳌是古代传说中的大龟或大鳖,一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列子·汤问》中,传说东海中驮着三座仙山的巨鳌;还有一种说法“龙生九子,鳌占头”。古代帝王要在宫殿前的石柱或在台阶上刻有鳌鱼的浮雕,以求天下永固之意。据传自唐代以来,考生在迎榜时,要让状元站在鳌头之上,称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鳌头就成为占首位或第一名的代名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起于隋代,而安东卫的第一位举人,却出现在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这一年安东卫有四位学子中举,这在当时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大事件,从此之后,安东卫举人进士日渐增多,康熙年间安东卫出了五位举人。鳌头山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安东卫志》中,这部志书是康熙十二年(1673)完成的,那时朝廷陆续开放海禁,鳌头山作为军事意义已经减弱,其文化意义就凸显出来。明清600年间,山东省录取举人进士共两万多名,其中12位状元。而岚山区范围内举人进士44名,安东卫这一个地儿就出了41位,最高等级是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解元赵应棋,只是乡试第一。日照一位状元焦竑籍贯则是西湖大花崖村。而“独占鳌头”的梦想,一直激荡在岚山区读书人的追求中。
这鳌头山海拔只有150米左右,因为坡度不大,很容易登上去。一到山顶,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安东卫志》中记载,这山顶多是“怪石苍松,峥嵘迭出”,倒也符实。从地质学上来说,这里地层属于新生界第四系,以酸性岩层为主的,学名称之为片麻岩,含有一种闪亮的晶体的那种,这是四万年前地壳火山爆发时形成的,所以形态各异,巧夺天工。
眼前的一块石头纹理是旋转的,中心形成扁圆的图案,还有一块巨石,端坐在一块巨石上,好像被劈了一刀,劈出来的那条石似长剑拔地冲天,这该是小“飞来石”了,大“飞来石”在东侧,匍匐在地。令我惊奇的是,这些巨石丝毫看不出长期风化的痕迹,倒像是不久才从另一块巨石中崩裂出来似的,而那块巨石又在哪里呢?我的目光很快捕捉到东南方向的一堆巨石,那是由十几块大小不同岩石叠加在一起,最上面一块顶面凸起,像是人工专门打磨似的,线条自然流畅,在这块巨石的前端,又有三块拼成一块近似椭圆的石头,面南向上微微昂起,整个形象像只巨大的海龟。当然,你还可以想象为其他动物,如像一只可爱的海象与巨型的狗狗。但我心里明白,这块巨石的名字一定是鳌头石,则是确定无疑。此时,再看“飞来石”,该是这鳌头石的“带刀护卫”了。
鳌头为什么成为先人的第一选择并且以此来命名整座山呢?
鳌头山的正南面就是浩瀚无际的大海,《安东卫志》记载:“在海南岸,上有石砚,俗传谓孔子观海处。”现在叫砚台山,古时称之为“孔望山”,就是说孔圣人曾经到这里“观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离此仅10公里的碑廓袁家庄村神童项橐,就曾与到这里巡视的孔圣人相遇,留下千古佳话,今天尚有圣公山,还建有圣公庙。孔子到这里“观海”,则是顺理成章的,再说曲阜到岚山距离本来就不远,也就是200多公里的路程,孔子到此巡视观海,完全有可能。鳌头山就面对着砚台山,在这个海拔高度上,看砚台山还格外真切。鳌头山的东面是笔山,又称之笔架山,因“两峰争出,形如笔架,故名”,明赵应元赋《笔峰春晓》云:“金乌才上晓山明,暖气浮春万象清;叠嶂矗霄真如画,天成景色即蓬瀛……”俗话“面对笔架山,不出文官出武官”,鳌头山东北侧是阿掖山,其南侧山峰下有面巨大石壁,有数百根条石整齐排列着,就像书卷排列起一样,那石壁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书架,此景点被命名为“万卷书”。鳌头山北侧的两座山,“巍峨峻拔,绂绕如椅坐”,一为轿顶山,二为与官山,顾名思义就有“出仕为官”的意思。鳌头山的西北方向,就是安东卫古城,古城里古时有文庙,经年香火缭绕热闹非凡。南门外有一眼“墨水井”,对这墨水井,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记忆,井壁青苍,往下观望深不见底,井水墨蓝色又泛着光泽,如墨汁一般。“鳌”本为龙之长子,而鳌头山的西侧是凤凰山,“龙起九州生瑞气,凤随云彩舞风华”,龙凤呈祥,吉利喜庆,多美好的象征!
这里有圣迹、有先师、有笔、有砚、有墨、有书卷……这些文化要素齐全了,古代读书人寒窗苦读经年,最高的目标“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儒风相高踏鹏背,士气自敢骑鳌头”,要出仕为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人将此石称为鳌头、将此山命名为鳌头山,最富有想像力,最为精当,堪称神来之笔。
有位文化名人说过,缺少文化底蕴的景观,即使能给人心灵的震撼,也是短暂的,真正能触动人心的,还是文化。鳌头山恰是这样的一例。这里有崇山峻岭,这里有茂林繁花,这里有海阔天空,这里还有岚山区人的文化基因,有着岚山区人的精神密码,这里有着能够触动你心灵的巨大力量。从古至今,独占鳌头的精神一直在激励人们争第一,占首位,去登顶,去闪耀,踔厉奋发,自强不息。这也是岚山区人民历经磨难、生生不息、越来越强的魅力所在!
鳌头山蕴含的精神极为丰富与宝贵,这鳌头山是上苍对这方水土的恩赐与惠顾。
站在山顶,感慨万端。半个月前,这里下过一场大雪,这雪已经融化,地面上留下密密的小孔还没有人的脚印走过。这里的空旷与寂寞,让我感到深深的惋惜。鳌头山与阿掖山是脉络相接地貌相同的,可是阿掖山人来人往,修环山路,建登山台阶,连上山的缆车、下山的滑道都有了,而这里呢?还是防护网拦截着不让上山。令我困惑的,在1994年出版的《日照市志》地理环境一章中,只记下了老爷顶(原名阿掖山)、笔架山、岚山、官山、轿顶山,连鲜为人知的“鹰山”都出现了,可是“鳌头山”竟然一字未提。国内一些文庙,还有“文昌阁”“魁星楼”等文化景点中,在某处建筑、某根石柱上刻有“鳌头”,那些莘莘学子与其家人,还络绎不绝到其跟前祈求与许愿,虽然这无比世俗,可也非常庄严的。而鳌头山这样一处天设地造的景点,竟然无人问津,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鳌头山不会寂寥下去,当代岚山人已经奋起。从民主革命家、黄埔四期的黄凤诏,山东护国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薄子明,到早期的共产党人士刘贤东、徐坦、赵明德,中国著名航天专家丁履德,全国劳模柴立清,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岚山人才,已经成群成批地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岚山正意气风发地向我们走来!
这只是一个精彩故事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