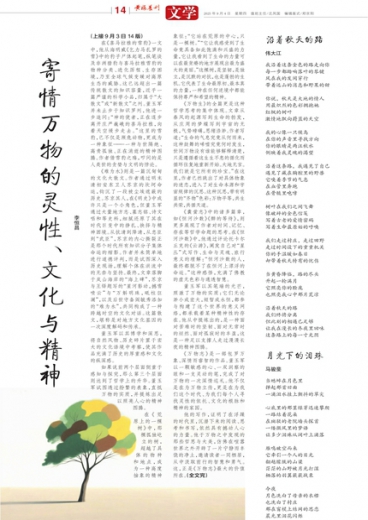|
寄情万物的灵性、文化与精神
李恒昌(上接9月3日14版) |
|
本文评论 评论数() 更多>>
评论正在加载中...
发布评论
|
|
更多>>
|
 |
 |
 |
|
本文所在版面
【第 A14 版:文学】
|
|
本文所在版面导航
·寄情万物的灵性、文化与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