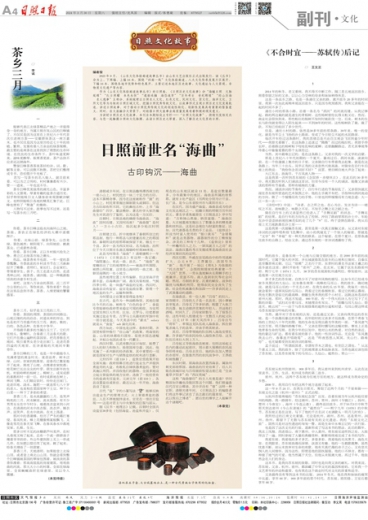王文正
1
2014年的秋冬,老父重病,我不得不中断工作,隔三差五地返回故乡,照看弥留之际的父亲,以让心力交瘁的母亲和妹妹稍得休息。
这是一条返乡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父亲的路。离开故乡20多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如此高频率地返回故乡,只是因为我预感到,我和父亲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通往小村的那条小路,沿着一条名为“涓河”的河流而建,从我记事起,路的两边栽的就是速生的青杨树。这些杨树曾经长得又粗又壮,然而,商业社会很快到来,那些粗壮的杨树不知何时被砍伐一空。后来,树木的生长与砍伐就变得让人陌生起来——不到30年的时间,这些杨树砍了栽,栽了砍,不知已经轮回了多少世代。
但是,通往小村的路,依然是30多年前的那条路。30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当年尘土飞扬的沙土路面,变成了今日轻尘不起的水泥路面。
每次开车经过这条路时,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会飞回到童少年时代———我曾光着脚丫,在这条路上追逐过“腾腾”而过的拖拉机;我曾手持长杆,沿着路边的杨树粘下吱哇乱响的夏蝉;还曾踟蹰路边,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心中偷偷爱慕的那个女孩经过。
当然,其中最难忘记的,是在这条路上,父亲对我的一次文学的启蒙。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暴雨过后,涓河水涨,滚滚向前。在一个恰逢镇上集市的日子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去赶集。就是在这条路上,当年三十出头、风华正茂的父亲忽然兴致高涨,对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说:“我给你念首词好不好?”说罢,便自顾自地大声念了起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无数次听到人们诵读这首词,但至今没有一个人的诵读,能像父亲诵读的那样有节奏感,那样有顿挫的力量。
然而,诵读诗词的节奏有了,自行车行进的节奏却乱了。父亲很快就沉浸在苏东坡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他的左手离开车把,手指伸向涓河流动的方向,做了一个缓慢而有力的手势,口里也同样缓慢而有力地念道:大—江—东—去……
《诗经•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骑在自行车上的父亲显然已经进入了“手舞足蹈”的状态。“手舞足蹈”的结果,是自行车的方向失去了控制,冲向了路肩厚厚的沙土中。车轮在沙中歪歪斜斜地扭麻花似的走了几个“S”后,终于歪倒在路旁,我从后座上无力地跌落在沙土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苏东坡,甚至是第一次真正接触父亲。从父亲对东坡诗词的沉浸吟唱和眉飞色舞中,幼小的我窥见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文学”和“幸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个秘密,在那个夏日,在那条通往故乡的公路上,经由父亲,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诗词透露给了我。
2
我的故乡,是鲁东南一个山地与丘陵交错的地方。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属于强大的齐国,齐长城就修筑在故乡的山地和丘陵间。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它以“琅琊”之名行于世,东晋时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乡就在这里;唐时开始有“密州”之称,在北宋,它属于京东东路密州府。熙宁七年(1074)九月,38岁的苏东坡卸杭州通判任,移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任地方长官。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自然少不了对密州风物的描写。比如今天已经成为家乡风景区的九仙山,比如鲁东南第一高峰的马耳山。我的故乡,确切地说,就是马耳山后的一个无名小村。在我生命的头15年里,我每天一抬头就会看到一道屏风似的马耳山,我看过它的春颜秋容,看过它的朝云暮雨,我也无数次登临它的最高峰,俯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远眺这块苍凉的密州大地。那时,我还不知道,900年前,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为它写下了无数的诗篇:“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由于与苏东坡修葺的超然台遥相对望,马耳山便这样成为苏东坡登台吟咏的对象。
当然,最早对于苏东坡的认知,还是通过父亲。父亲向我传达的苏东坡,是一个浪漫而豪迈的形象。而年轻时的父亲多才而浪漫,在那个青春飞扬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的生命也呈现出最为华美的一面。“春风意气长空万里,明月胸怀皓魄千秋。”父亲在那时撰写的这幅对联,事实上正是他青春生命的写照。在我少年的认知中,他对山水的热爱,对自然的亲近,他的豪迈与旷达,都有着东坡的影子。他的一些诗词作品,无论是“东风邀我去山行,春幕连开唱晓莺”,还是“昨夜悠悠入冥冥,关山行,路难穷”,也无疑都受到东坡诗词的影响。
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故乡,除了它的地理意义和血脉亲友,当然也就应该包括了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笔下的马耳山、九仙山、超然台、常山……
3
苏东坡从杭州到密州,900多年后,我从密州来到杭州求学,从此在这里读书,工作,生活,杭州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密州,杭州,这两个苏东坡为任地方官的地方,就这样成为我命定的乡愁。
2009年,我用自行车把这两个地方连接了起来。
这一年9月24日,在我生日那天,筹划了近两个月的“千里单骑——东坡文化之旅(杭州—密州)”正式启程。
从杭州苏堤南端的“苏东坡纪念馆”出发,沿着东坡当年从杭州赴任密州的线路,我一路骑车,经过湖州、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今淮安)、海州(今连云港),最终返回故乡,并于10月3日中秋节那天到达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超然台”—— 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节,苏东坡正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千古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我所经过的江南文化重镇,无论是杭州、湖州、苏州,还是常州、润州、扬州,都留下了无数与苏东坡有关的文化遗迹。我的“东坡文化之旅”,固然只是对这些遗迹的匆匆一瞥,却是生命中永难忘记的一次行旅。
也是因了这次文化的行旅,逐渐形成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此后的数年,我北上凤翔,西进眉山,南下惠州,中入黄州,将东坡足迹所到之处,大致拜访了一遍,同时参阅了大量的典籍资料,断断续续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我爱东坡。我爱他的多才多艺,多姿多彩,我爱他的光风霁月,海色天容。在我眼里,苏东坡浪漫而深情,诙谐又有趣。他的一生载歌载舞,虽然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他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又有悲天悯人的人间情怀。因为这些,即便是他的固执倔强,他的口不择言,都有一种接了地气的可爱。他当然属于天空,但他从未脱离大地。再过千年,他依然会在人们的身边。
这本书,是我向苏东坡的致敬,同时也是向我父亲的献礼。对我来说,苏东坡、父亲、杭州、密州,都深藏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它有我一个文艺青年的冲动和虚荣,也有我在这个商业时代对文化的珍重和追寻。
父亲最终没有等到这本书的出版。2014年冬天,他在我和妹妹的痛哭中长逝,享年66岁。9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都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