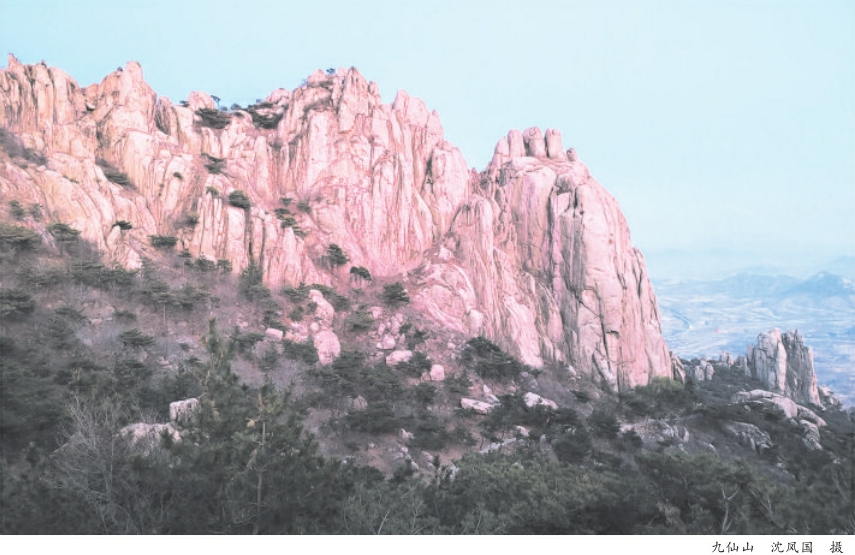|
在日照遇到苏轼
张克奇 |
|
本文评论 评论数() 更多>>
评论正在加载中...
发布评论
|
|
更多>>
|
 |
 |
 |
|
本文所在版面
【第 A4 版:海曲文学】
«上一版
»
|
|
本文所在版面导航
·在日照遇到苏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