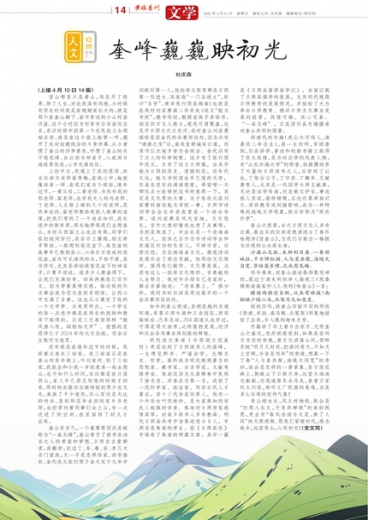杜庆森
(上接4月10日14版)
登山哪里只是看山,而是开了眼界、悟了人生。对此我深有同感。小时候有很长时间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就是那个在奎山脚下、崮河旁边的小山村崮河崖。这个小村因为村旁有吕母崮而出名,东汉时期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女领袖吕母,就是在这个崮上振臂一呼,揭开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序幕。从小看惯了奎山的四季景色,听惯了奎山的关于莲花峰、白云洞与神屋子、八戒洞与海眼等传说,心中充满向往。
上初中后,我遇上了我的恩师、班主任语文老师翟秀梅,在我心中,她就像母亲一样。在我们家有个规矩,逢年过节,一看父母,二看老师。当然有我的郭老师、翟老师,也有我夫人的刘老师、丁老师。人生路上碰到几个好老师,是很幸运的。翟老师教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追求知识、成长进步的新世界。周末她带领我们去爬奎山,当时从西面上山也没有路,同学们在松枝间穿行,在岩石上攀爬,相互牵手帮助,一路爬到莲花盆下。莲花盆的故事早已熟稔在心。六块巨石组成的莲花盆,盆内可见清冽的水,不枯不腐,甚为惊叹。尤其是讲钻进莲花盆下的神屋子,只要不说话,进多少人都盛得下,让我们充满好奇。回来再教我们写作文。因为带着真情实感,每次我的作文都会成为范文在班里朗读,让我心中充满了自豪,这也从小奠定了我的一个文学梦。后来更明白,一个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师长的鼓励和教导下取得的,正是三月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遗憾的是恩师已于2024年的元旦仙逝,空余后生慨叹与追思。
还有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跟着父亲走三姑家,我三姑家正是在奎山的东半坡上,叫刘家村。到了三姑家,我就会和小我一岁的表弟一起去爬山。也不知什么时间,往往都是在日落西山,家人早已酒足饭饱的时候才回来。那时的衣服往往被树枝刮得少皮无毛,虽挨了不少埋怨,但心里还是无比的快乐。直到师范毕业回到家乡当老师,也经常约着同事们去上山,有一次还进了防空洞,在里面转了好久才出来。
奎山有名气,一个重要原因还是被称为“一县文峰”,奎山寄予了读书求功名之人的希望和梦想。日照自古重耕读,尚勤学,出过丁、牟、秦、安、李几大名门望族,无一不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金代状元张行简于金大定十九年中词赋科第一人,他的祖父张莘卿是日照第一位进士。其家族“一门五进士”,世曰“五贤”。晚年张行简在城南(也就是在我村刘家寨南二华里处)设立“魁文书院”,教书传经,教授家族子弟读书,相交四方文人雅士,境况可谓繁盛,这是开日照文化之先河。我村奎山刘家寨据传是因金代的兵寨而设村,因为北宋“靖康之变”后,南宋皇朝偏安江南,而淮河以北地方皆为金统治。金代沿用了汉人的科举制度,这才有了张行简中状元,才有了设立日照镇,后来升格为日照的历史。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魁文书院遗址早已荡然无存,但县志里写的清清楚楚,希望哪一天哪位名士能够把这书院复原一下,肯定是文化界的大事。关于张状元在刘家寨村南设魁文书院一事,日照市诗词学会会长辛崇发曾在一个场合夸赞,说刘家寨是风光宝地,文化悠长,言外之意好像我也受了点熏陶,当然是戏说了。辛会长是一个老海曲文化人,退休之后作为市诗词学会和东港区作协的负责人,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弘扬海曲文化,推进诗词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那份文化情怀,值得我们敬仰。文化要发展,必须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情怀、有奉献的人去努力。我对外介绍自己老家时,都会自豪地说:“老家寨上。”据分析,我村当时应该是周边最早的一个由兵寨而设的村。
如今的奎山街道,坐拥优越的交通环境,东靠日照大港和工业园区,西邻高铁站、汽车总站,204国道从此穿过,可谓是得天独厚,必将蓬勃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再创新的辉煌。
明代状元焦竤(今西湖大花崖村)更是达到了日照读书人的高峰,一生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文史、哲学,最终成为明代晚期著名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焦竤还因为从落榜卷中发现了徐光启,并亲点为第一名,成就了一代科学家、政治家。而其后代人才辈出,其十三代孙是位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是大家熟知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焦竤对日照老家感情深厚,对家乡读书人多有教诲。明代日照县共考中含焦竤进士9人,有两名是焦竤的学生。在《日照县志》中保存了焦竤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日照县重修庙学记》,全面记载了日照县儒学的发展,尤其明代晚期日照教育的发展情况,并描绘了大力举办日照教育、推动日照文化事业发展的前景,其情可敬,其心可嘉。“一县文峰”,正是历任县志编撰者对奎山共同的期冀。
到清代的许瀚(虎山大河坞人,清嘉庆二年出生),虽一生坎坷,穷困潦倒,但在讲学、著述和校勘书籍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是当时北学的代表人物,有“山左许瀚之学”的称誉。他提携培养了大量的日照读书之人,后世的丁以此、丁惟汾父子,丁守存、丁麟年、王献唐等人,尤其是一代国学大师王献唐,无论是治学传道,还是敬文护宝,事迹感人至深,堪称楷模,后边还要单独记之。受其教导或间接影响,成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学现象,被后世称为“照邑朴学”。
奎山之胜景,古之日照文化人多有记载。最出名的应该是晚清进士丁泰作咏题诗《登奎山》,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极为壮观的山水画长卷:
沙浦山无数,来斯刮目看。一拳称砥柱,千古障狂澜。人与星共聚,海随天自宽。登临莫长啸,足底有龙蟠。
而今看来,对奎山描述最形象传神的,莫过于清末明初举人高祝三(现秦楼街道高家村人)。他的《咏奎山》一首:
瞻彼西旗空自飘,从来有谁敲?南鞍缺少随心马,北架恐无如意毫。
短短四句,将奎山四面不同的形状(西旗、东鼓、南马鞍、北笔架)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令人感到趣味无穷。
开篇讲了早上看日出东方、光照奎山之盛况,忽然就感觉到,如果是在明月当空的夜晚,看月光洒满山间,领略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的意境,想象一下丁泰“人与星共聚,海随天同宽”的奇妙,该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坐于莲花峰上,俯瞰山下日新月异,远望大海波光粼粼,近观道路车水马龙,喜看万家灯火闪烁,聆听工厂机器的轰鸣,当是多么壮观的宏伟气象!
青山绿水长,风正好扬帆。既会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更会有“春风浩荡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无限感慨。愿我们紧随时代,感念故乡,远望青山,心有初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