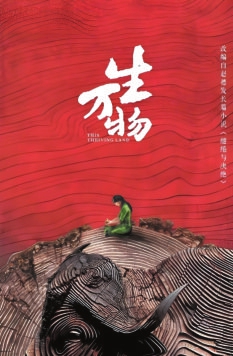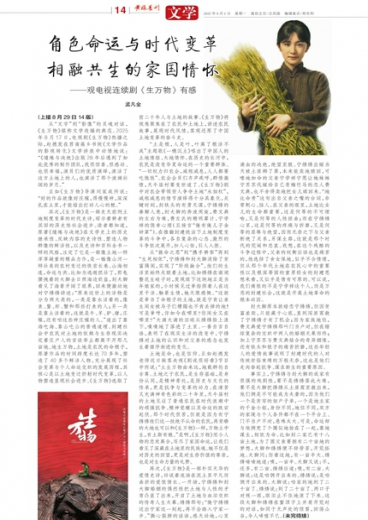孟凡金
(上接8月29日14版)
从“文字”到“影像”的灵魂对话,《生万物》堪称文学改编的典范。2025年8月17日,电视剧《生万物》热播之际,赵德发在莒南高乡书院《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文学讲座中动情地说:“《缱绻与决绝》出版28年后遇到了如此优秀的制作团队,我很惊喜、很感动、也很幸福,演员们的优质演绎,演活了这方土地上的人,也演活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岁月。”
正如《生万物》导演刘家成所说:“好的作品就像好庄稼,得慢慢种,深深扎在土里,才能结出打动人心的粮。”
其次,《生万物》是一部史无前例土地制度变革的时代史诗,昭示着耕者有其田的历史性社会进步。读者都知道,原著《缱绻与决绝》在文学史上的历史继承性、反映内容的史诗性、塑造人物群像的鲜活性,以及史诗和百科全书一样的风格,注定了它是一部像土地一样浑厚凝重的精品力作,是一幅像山河一样壮美的农村变迁的恢宏长卷。山海相连,命运与共。比如为逃避抓壮丁,郭龟腰拽着封大脚去日照海边贬盐,封大脚看见了海景开阔了眼界,回来便激动地对宁绣绣讲述:“原来这世上的活物是分为两大类的,一类是靠水活着的,像鱼、鳖、虾、蟹和那些打鱼的人;另一类是靠土活着的,这就是牛、羊、驴、猪,庄稼,还有咱这些种庄稼的人。”道出了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的普通道理。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生存现实决定着庄户人的言谈举止都离不开那几亩地。地生万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原著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70多年,塑造了40多个鲜活人物,充分展现了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发展历程,其核心是以土地变迁折射时代变革,以人物塑造显现社会进步。《生万物》选取了前二十年人与土地的故事。《生万物》将视角聚焦在了农民和土地上,讲述农民故事,展现时代风情,客观还原了中国土地变革的奋斗史。
“土是根,人是叶,叶离了根活不成”主题歌《一穗沉土》唱出了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大地情怀。在历史的长河中,农民是改变华夏命运的一个重要群体。“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人人都要吃饱饭”。农会会员们齐声疾呼,群情激愤,天牛庙村要变世道了。《生万物》剧中对农会带领穷人争夺土地“永佃权”,减租减息的情节演绎得十分具象化,关键时刻,封铁头的有勇无谋,宁绣绣的善解人意,封大脚的奔波周旋,费文典的左右为难,费左氏的精明算计,宁学祥的侥幸心理(且扬言“俺有俺儿子金钟罩”)。在推翻封建统治下土地制度变革的斗争中,各自复杂的心态、激烈的斗争依次展开,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从“救命之恩”到“携手耕犁”再到“生死相依”,宁绣绣和封大脚消除了贫富隔阂,实现了“阶级融合”,他们的生活里始终关联着土地。比如绣绣在南湖整花生畦子时,发现眼下这块地正是当年娘家的,小时候见过爹指挥着人在这里干活。触景生情,她无限感慨。“这就是爹当了命根子的土地,就是宁肯让亲生闺女被马子们糟蹋也不肯丢掉的地!可是爹呀,你如今在哪里?你闺女又在哪里?”大滴大滴的泪球从绣绣脸上滚下,噗噗地了落进了土里。一番自言自语,表明了在现实生活的改变中,宁绣绣对土地的认识和对父亲的感念也发生着循序渐进的变化。
土地是命,也是信仰。正如赵德发老师近日做客央视《剧说很好看》节目中所说:“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土地之于农民,是生存基础,是身份认同,是精神寄托,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更是抗争与变革的动力。在清苦又充满神奇色彩的二十年里,天牛庙村的土地见证了普通农民在时代浪潮中的顽强抗争、精神觉醒以及命运的跌宕起伏。那个时代很苦,但就是因为有宁绣绣他们这一批绝不认命的农民,再贫瘠的大地也可以和《生万物》一样,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是啊,《生万物》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写尽了家国命运,让我们看见了深藏在土地里的民族魂。她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生存价值的尊崇,也是对生命力量的礼赞。
再次,《生万物》是一部朴实无华的爱情史诗,诉说着流淌在泥土里平凡而曲折的爱恨情长。一开场,宁绣绣和封大脚婚姻的偶然性把土地与人性的矛盾凸显了出来,开启了土地与血泪交织的传奇人生大幕。绣绣那句:“俺宁绣绣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撕心裂肺的话语,感天动地,心里滴血的决绝,绝望至极。宁绣绣出嫁当天被土匪绑了票,本来能卖地赎回,可嗜地如命的父亲宁学祥宁愿让她妹妹宁苏苏代嫁给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费文典,也不舍得卖地把女儿赎回来。“地比命贵”这句出自父亲之嘴的台词,非常刺心、恼人。在父亲的眼里,土地比女儿的生命都重要,这是何等的不可理喻,又是何等的人性扭曲;而在宁绣绣心里,这是何等的疼痛与折磨,又是何等的屈辱与绝望,因而无奈之下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另谋生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悲哀。我想,在这个残酷的斗争过程中,父亲的权衡应该也是痛苦的,他选择了舍女保地,似乎不合情理,但从那个年代土地在农民心中的重要性以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来看,又似乎是情有可原的。可以说,我们痛恨的不是宁学祥这个人,而是万恶的封建社会,这就是开展土地革命的根本动因。
封大脚原本就暗恋宁绣绣,但因贫富差距,只能藏于心底,直到闯匪窝救了宁绣绣才有了机会;因为家族地位,费文典爱宁绣绣那叫门当户对,但在错综复杂的交织中两人的婚姻无果而终;加上宁苏苏与费文典结合的奇异姻缘,还有铁头和银子的痛苦折磨,这些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说明了封建时代的人对传统世俗束缚的万般无奈,这也是他们走向奋起抗争、谋求新生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宁绣绣与封大脚的成家有很强的戏剧性,要不是绣绣落此大难,要不是大脚把绣绣从土匪窝里救出来,他们俩是不可能成为夫妻的,因为他们一个是贫穷的佃户子弟,一个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双方的家境与个人条件都不在一个平台上、门不当户不对,悬殊太大。可是,命运却与他俩兜了个圈似地拴在了一起,靠地谋生,相依为命。比如封二家已有十八亩土地,为了圆父亲要拥有二十亩地的梦想,大脚和绣绣便不辞劳苦,开荒拓地。大脚问:你看这地,有一亩半大。绣绣喃喃地道:噢,一亩半。大脚又说:不,还多,有二亩。绣绣应道:噢,有二亩。大脚说:这是咱俩开出来的。绣绣说:是咱俩开岀来的。大脚说:咱家的地到了二十亩了。绣绣说:到了二十亩了。两口子对视一眼,眼泪止不住地滚了下来。这段大脚和绣绣在鳖顶子上并肩开荒时的对话,如同于无声处的惊雷,回荡山谷,令人唏嘘不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