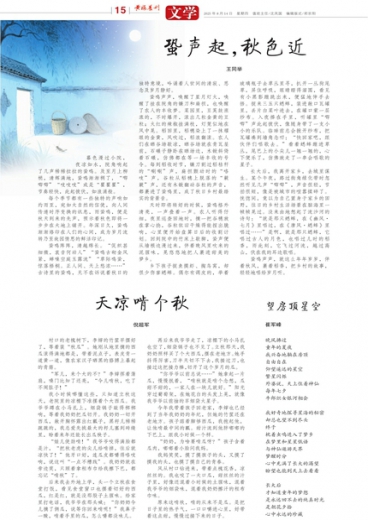|
蛩声起,秋色近
王同举 |
|
本文评论 评论数() 更多>>
评论正在加载中...
发布评论
|
|
更多>>
|
 |
 |
 |
|
本文所在版面
【第 A15 版:文学】
|
|
本文所在版面导航
·蛩声起,秋色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