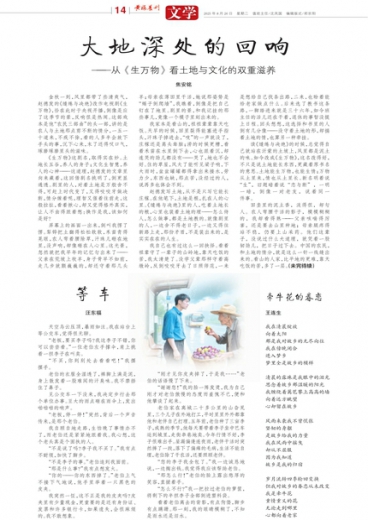|
大地深处的回响
——从《生万物》看土地与文化的双重滋养
焦安铭 |
|
本文评论 评论数() 更多>>
评论正在加载中...
发布评论
|
|
更多>>
|
 |
 |
 |
|
本文所在版面
【第 A14 版:文学】
|
|
本文所在版面导航
·大地深处的回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