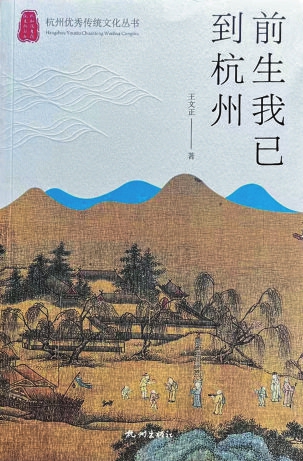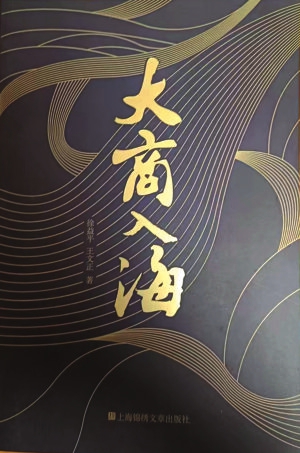全媒体记者 沈凤国
编者按
作为研究苏轼的学者,王文正出版了苏东坡传记著作《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有关苏东坡与杭州的著作《前生我已到杭州》以及将要出版的《东坡语文》。
他自谦为苏轼的“粉丝”,他对苏轼不只是研究,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召唤,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追寻”。苏轼对于他而言不是客体,而是生命的连结。2009年,王文正骑着自行车从杭州到密州开始了第一次的“东坡文化之旅”,从此他开始真正走入苏轼的世界。
他另辟蹊径,注重苏轼和地方的关系,将苏轼的生平与其所经历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现中国工程院院士)读过《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一书后,评价“你比大多数搞文学研究的人,都更早地注意到了作家与地理的关系”。
为什么取名“不合时宜”?到底应该如何解读苏轼?王文正认为所谓“不合时宜”,就是深情守望,寻求远方,不放弃精神的方向,在众声喧嚣之际以沉默对抗庸常。
请读者同我一起走进王文正的苏轼世界。
人物简介
王文正,1972年生于山东五莲,生活于杭州。独立作家,记者。天都书院院长,杭州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江南文化和浙商研究。2015年出版的苏东坡传记著作《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一书,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买断音频版权,并连续播出81集。有关苏东坡与杭州的著作《前生我已到杭州》被列为“杭州市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另有《大商人——— 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笑傲商海》《大商入海》等作品,参与撰写《杭州简史》。2024年1月即将出版有关苏东坡研究的第三本著作《东坡语文》。
记者:近几年,全国不同地方都悄然兴起了“苏轼热”,热爱苏轼和研究苏轼的群体都较前些年有了很大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目前全国的苏轼研究是何状态?
王文正:这几年的“苏轼热”,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与国学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受到了重视,一些主流媒体搞的诗词大会之类,也在大众层面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苏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传统文化的高峰。苏轼是一个全才型的士大夫,在文化方面,他在诗词歌赋书画等方面都有杰出建树,甚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同时他仕途坎坷,在熙宁变法期间与王安石的斗争,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在舆论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乌台诗案成为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文字狱,他同时又是元祐党人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苏轼并不高高在上,他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在生活方面有着许多创造性的东西,诸如美食、酿酒、品茗、赏花等,都影响了身后中国人的生活趣味。苏轼这种本身的丰富性,是“苏轼热”的内因。当然,“苏轼热”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苏轼身后,历代文人对他崇拜有加,他们以各种方式向苏轼致敬,把苏轼写入书中,编进戏曲中,甚至形成了在每年苏轼生日那天,举行纪念苏轼的“寿苏会”。
“苏轼热”总体来说,对于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对艺术审美的提高,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都有正向作用。当然,如今的“苏轼热”也有“隐忧”:那就是它有大众流行文化的趋势和倾向,一些博主片面地解读苏轼,将他“鸡汤化”,只强调他洒脱乐观和多才多艺的一面,却无视他为民请命、“对权力说不”的人格精神,很多人津津乐道苏轼的才华,却不敢或不愿提及(更不用说践行)他的人格精神,是有失偏颇甚至有害的。
苏轼研究方面,代不乏人,一直有传承。学院派中有王水照、曾枣庄、孔凡礼等杰出学者,近些年张志烈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王水照的弟子朱刚的《苏轼十讲》都是很不错的成果。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一些苏轼的“超级粉丝”如台湾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李常生先生的《苏轼行迹考》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苏轼研究这条路的?和您的故乡马耳山有何内在关联?
王文正:我于苏轼,不敢说是“研究”,只能算是一个“粉丝”向他的致敬吧,我曾说过我于苏轼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召唤,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追寻”。苏轼不是我拿来研究的“对象”,他于我不是客体,而是生命的连结。这种生命的连结,确实起始于故乡马耳山后的那个小村庄,与父亲有关,与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屋有关,与发源于马耳山的涓河有关,与五莲山(九仙山)上苏轼“奇秀不减雁荡”的题词有关(详见《不合时宜》书中后记与《东坡语文》书中前言)。苏轼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但是直到到了杭州后很多年才算成长起来。
有些事情其实是自己不曾注意到的。七八岁时父亲在自行车上对我进行了一次苏轼与文学的“启蒙”,三十年后的2009年我骑着自行车从杭州到密州开始了第一次的“东坡文化之旅”,从此开始真正走入苏轼的世界。自行车成为一个其中的连结,这一点我此前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而是日照评论家协会孙明霞秘书长发现了这一点,还是很有点意思的。
记者:您倾心五年,沿着东坡足迹,行程数万里,拿出了《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这本书,我看到豆瓣评分8.2。您将研究苏轼的专著取名“不合时宜”,用此四字统领整书的基调,观照整书的主旨。为何选择用这四个字而不是苏轼别的许多经典语句?
王文正:感谢您提出这么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其中可以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父亲,他的一生完全可以用“不合时宜”来总结。父亲虽然一生生活在农村,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作为个体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对社会有一种理想主义,为人处世又是道德主义。这样的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很难生存的,他有才华,却让家里十分拮据,也让家人特别是我母亲在经济上、生活上吃了不少苦,这都是他“不合时宜”的性格造成的。年轻时我曾为此与父亲发生过冲突,但日后随着年岁增长,对他有了一些理解。《不合时宜》这本书的初稿,是非常散文化的、不守规矩的写作,有好几个段落写了我父亲的一些诗词,但在后期觉得它太不像“一本书”,后来就把那些段落都删掉了。“不合时宜”这个书名,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是我对苏东坡的爱妾王朝云的偏爱。这本书中,其中有一篇《惟有朝云能识我》,其实是整本书写得最早的一篇。这一篇写于2009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是我“东坡文化之旅”结束,回到杭州不久写的。当时看了一些资料,朝云的一些事情感动了我,似乎来了灵感,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了这篇,当然那其中也有我本人的一些感情的抒发。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我认为是对苏轼性格最为中肯的评价。包括现在,许多人都多注意苏轼的才华,苏轼的乐观,但却常常忽视他的“不合时宜”。是因为他的“不合时宜”,才造成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因为有这种大起大落,才有了他充沛的生命的势能,如同瀑布从高处落下,才会产生生命诸多的壮丽和色彩。
在我看来,所谓不合时宜,就是在一个薄情的时代里深情地守望,在一个苟且的世界里寻求着远方,在物欲横流之时不放弃精神的方向,在众声喧嚣之际以沉默对抗庸常。从古到今,这种“不合时宜”的人都是少数。
第三个原因,就是作为书名,又要概括苏轼一生,又要与苏轼本人有关的语句,其实也并不多。可能“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最适合的一句,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句,但这个句子用得太多了,几乎烂大街了,我抛弃了这个选项。当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我比较偏爱。封底用了邓石如的一方印章“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是我选出来的。
记者:从古代行政区域划分上看,日照市五莲县属于古密州,苏轼的具体生命行踪和文化行踪都为古密州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密州对苏轼文化轨迹的发展演变影响很大,甚至是他的文学艺术风格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从目前看到的大多数苏轼传记来看,对苏轼密州两年记述的篇幅都十分有限。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王文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在写《不合时宜》这本书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能给出的解释,只能是以前的学者不太注重作家与地方的关系吧,我可能是比较早(不敢说最早)的把一个传主的生平与他所经历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但在书的副标题中这么说明,而且是以地方表示每一章,贯穿其一生。记得2015年6月本书刚出版时,由于一个机缘,我拿给老校长———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现中国工程院院士)看时,他有一句评价,说你比大多数搞文学研究的人,都更早地注意到了作家与地理的关系。
密州之于苏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站。仕途上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任一把手知州的地方;从政绩上来说,他在密州领导抗蝗抗旱,也是他真正意义上为民请命、报效国家的开始;从文学上来说,他在密州开创了词史的两大流派之一的豪放派,他在密州写的《雪夜书北台壁二首》形成了诗史上有名的“尖叉诗韵”;思想发展来说,在密州,他的“超然”思想趋于成熟。可以说,没有密州的苏轼,就没有黄州的苏轼。或者说,没有苏轼的密州,就没有苏轼的黄州。此前学者多注重黄州的苏轼,却忽略苏轼的密州,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在《不合时宜》密州一章中,有意识地强调了苏轼对密州文化的贡献。
记者:密州和杭州,是“东坡人文地图”中的重要转折点。您出生于古密州,生活于杭州,恰好暗合了苏轼的人文地图轨迹的一部分,这对您、尤其是对您研究苏轼有何影响?
王文正:对“研究”的影响我不敢说,但至少有一点,对“生活”的影响是时时刻刻的。大学之前都在故乡密州,家就在马耳山后,抬头就可“前瞻马耳九仙山”,这是苏轼的诗句。从小喜欢游山玩水,1988年“五一”第一次到五莲山游玩,看到“奇秀不减雁荡”的题刻,就心生有朝一日去雁荡山看看的愿望,到1998年“五一”真的去了雁荡山。人生真是很奇妙的事情,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概率是真的。因为从小向往江南,喜欢诗词中的杭州,终于也是生活在了杭州。杭州是苏轼唯一两次为官的地方,这里的城市与山水都承载着关于他的记忆,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山间水际,总是会与苏轼相遇。而杭州周边的江南一带,湖州苏州常州镇江扬州,都是苏轼多次来回经过的地方,现在开车数小时就可到达。如果“研究”不只是局限于书本,而包含对他人生的体味的话,那生活在苏轼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那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从“时间单元”上看,苏轼和我们处于同一个“时间单元”。他是入选法国《世界报》的“千年英雄”。现在,你的家乡日照正在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个“千年英雄”的文化,将苏轼这个巨大的文化品牌融合到文旅事业中去,请您提一下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王文正: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一个地方的发展,官员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苏轼,我们首先要还原他的一个身份,就是官员。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文人,第一要务是做官从政,而不是诗词创作,只有少数作家没有做官,也只是因为科举失败,没有办法而已,这一点其实是被很多当代人给忽略了。那么像苏轼这些士大夫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升官发财吗?当然不是。这些优秀的士大夫的做官的目的,无非是实现儒家理想,是致君尧舜,是济世救民。再简单一点来说,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做了这些,也就等于报效了国家。因此,“东坡热”中,首先应该向苏东坡学习的,是官员,即学习他为百姓着想,为百姓谋福利,为百姓做实事的精神。一个地方有了更多苏轼这样敢于担当、敢于做事的官员,有更多这样的官员,这个地方就会有了发展的希望,文旅事业也一定会发展起来。
苏轼在密州为官三年,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遗产。五莲及今天日照的很大一部分,也都属于宋时密州的辖区。但是如今这一块地区,与密州州治所在地诸城在行政辖区上分开后,五莲及日照在“密州东坡”这一块有点“吃亏”,也就是说,苏轼在五莲及日照留下的文化资源略显单薄。但是,五莲日照又有着诸城所缺乏的资源,那就是山水资源。特别是五莲山九仙山,秀美天下,在整个齐鲁大地是屈指可数的,在今天人们日益渴望回归自然山水的背景下,这样的资源既得天独厚,又十分稀缺。而五莲这两山到日照海滨也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山海连接,又有苏轼的文化资源,这又是诸城所不能具有的。我认为要发展五莲、日照的文旅事业,首先要紧紧地聚焦五莲山、九仙山以及日照海滨这独特的自然资源,实行山海联动;其次应该打开眼界,打破行政地域界限,与诸城联动,将那些因慕东坡之名去诸城游览的人们,引到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甚至日照海滨;还可以与富庶的温州雁荡山结对,共同举办一些活动,互相引流;把长三角的客人吸引过来,特别是在京沪二线高铁开通后,这一点尤为重要。发展文旅事业,一定是要赚外地人的钱,仅靠“内循环”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丁家楼子村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优势,这个优势除了苏轼题写摩崖石刻“白鹤楼”,还有丁惟宁。苏轼与丁惟宁之间是否有内在的隐性的精神血缘关系?
王文正:很抱歉,我对丁惟宁涉猎不多,这个问题不敢乱说。
记者:出于实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瓶梅》作者极有可能就是丁惟宁。针对当代学界的这个论述,请谈一下您的体会。
王文正:《金瓶梅》是明代小说的高峰,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今天看来,把《金瓶梅》视为淫书并加以禁止,甚至不能谈论,是过分了的。把这样一个文学艺术的宝藏人为地埋葬,没有必要。
把丁惟宁视为《金瓶梅》的作者,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证据并不够全面,但是相比其他作者的说法,“丁惟宁说”却更具竞争力,这首先是因为丁耀亢有《续金瓶梅》,这个学界没有争议,另一点是其中有大量的方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稍具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区,是很难熟练地运用当地方言的。《金瓶梅》作者的“丁惟宁说”,固然证据还不够丰富,但要推翻他同样困难。这一点,对五莲十分有利。今天各地对文化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五莲、日照不应该轻易放弃。如果“丁惟宁说”在学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就可以做很大的文章。这样,中国古代小说,短篇有《聊斋志异》,长篇有《金瓶梅》,两大高峰都在山东,对整个山东的文学资源都是十分有益的。